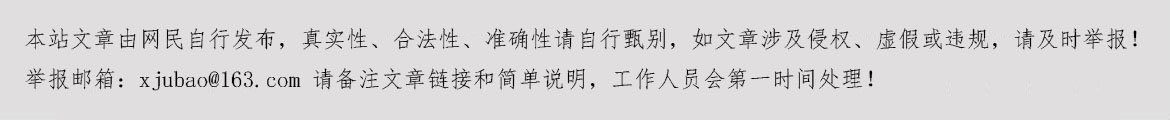yy影视在线看最热影视 https://www.516.run
“自我”与“他者”:中日关系中的身份认同
作者:Dr. Shogo Suzuki,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外交政策、日本外交政策、中日关系和民族主义。
导读
中日关系作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长时间处在一系列政治、历史、经济、安全问题的议论中心。在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中,中日关系甚至形成了“政冷经热”的状况。本文从“自我-他者”的辩证角度,考察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如何在与西方大国和日本的互动中形成的,提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构的“受害的自我”以及日本“施害的他者”的形象,重新解释了历史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中国国家自我认同建立背后的政治学根源。本文将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负面历史记忆,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认同的形成,更加明确地联系起来,为中国国家认同和中日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重要的是,本文认为日本右翼知识分子将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中国政府,甚至希望免除日本的历史责任,这是令人不齿的。因为这种态度只会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日本真的想与它在东北亚最重要的邻国建立更稳定友好的关系,就需要认真地对待其罪恶的历史,并对中国的“自我”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摘要
近年来,很多研究指出中国将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作为对日谈判以及处理国内政治问题的工具。对此,作者认为,这一论点未能理解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负面记忆对中国影响的深刻程度。本文通过将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置于中国国家认同中,提出了另一种论点。作者认为,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的特征是“受害者(victimhood)”意识,这是在与国际社会的频繁交互中产生的,而日本作为一个“他者(Other)” 在增强中国作为“受害者”的自我认同 (self-identification)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后,日本作为“他者”出现在中国的国家认同中,是中国试图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社会里恢复其社会制度和道德合法性的一个副产品(by-product)。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用以塑造身份认同的工具,国家本身作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s)更是深受历史的影响。
引言
2005年,日本政府担心中国民间的反日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关系密切,这种观点呼应了近期中日关系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假定政治决策者可以合理地将历史用作政治工具。本文认为,上述论点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日关系,因为它们不仅将中国民众弱化为极易被官方操纵的对象,而且没有正确理解中国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所带来的负面记忆的内在本质。理解中日关系,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尊重并正视历史记忆的态度。因此,本文试图利用身份形成的“自我”和“他者”辩证关系(‘Self’ and ‘Other’ debate)来研究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日本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本文的论点有三个部分:首先,国家及其人民是道德主体,他们的行为受到历史记忆的强烈影响。日本在中国的负面形象并不是近些年来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中形成的。其次,中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经常被视为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价值观相悖的“他者”而受到怀疑。最后,日本作为“他者”出现在中国的国家认同中,是中国试图维护其“受害者”身份,并在一个仍有“核心”和“边缘”之分的国际社会中重新获得其社会和道德合法性的副产品。
历史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传统解释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大致有两个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日本的入侵行为所造成的创伤性经历(traumatic experiences)在中国人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任何行动都带有日本未能正视过去的意味和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隐喻。因此对于这类行动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记忆的“下意识反应”(‘knee-jerk response’)。
第二种解释则认为,中国战略性地“利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具体而言,中国利用日本的战争罪行,从而使东京做出政治让步。此外,在中国内部,历史被用来支持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立场,从而增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这一论点确实抓住了中国近期反日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作者认为它具有以下三个缺点。首先,反日情绪(anti-Japanese sentiment)本身并不一定是被故意传播的。考虑到日本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刻意宣传反日情绪本身并不“经济”。其次,如果承认他们战略性地利用历史记忆的能力,则意味着领导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于历史记忆,并且可以操纵历史以满足当前利益。然而,在现实中许多人都有与日本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很难想象他们能够脱离自己的历史记忆。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战略性地利用和操控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也只有在该观点与听众取得广泛共鸣时才会有效。也就是说如果人群中不存在某种形式的反日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就很难从历史记忆中产生。因此,历史并不是只有在政治精英寻求其政治利益时才成为重要的工具,而是更加深刻地根植于中国社会之中。将反日情绪的产生和发酵简单归结为“操纵”和“利用”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更好地解释历史的其他理论框架。
作者引用了石之瑜(Chih-Yu Shih)的观点。回到中国近代史,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中国传统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文化实体(cultural entity)”而非“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即便是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这种威胁的产生仍然可以从文化层面加以解释。然而,日本作为一个与中国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其崛起与扩张事实上对中国的生存而不是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威胁。通过这种方式,日本作为一个对中国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自我认同。“他者”概念的引入对重新思考中日关系的历史开辟了新的途径。一方面它让我们深入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在构建现代中国国家认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为理解反日言论在当今中国产生的“共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开端。
身份、自我和他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受害者”身份
根据建构主义观点,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而建构自身的身份取决于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创立并维持一条界线1。也就是说自我的含义不能只由狭义的“内部群体(in-group)”赋予,还必须由更广泛的“外部群体(out-groups)”赋予。由于身份总是根据与他者的差异来建构的,而他者与主体的“差异”程度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身份形成有一个主体间进程(intersubjective process),即社会行为者无法事先确定自己的身份,只有通过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才能形成对“自我”的认识。与多个“他者”的互动将导致各种不同的、重叠的自我认同形式。哪种特定的身份会凸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者在某一特定时刻与哪个“他者”互动。具体到对中国国家认同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受害者”身份可以从近代一直持续到今天,然后分析日本在这种特殊身份形成过程中如何成为“重要的他者”。
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中国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碰撞密不可分。古代中国是作为文化实体的自我认同,不是被限定在一定边界之内的“国家”。而在近代大量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很多人意识到了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受西方民族主义观念影响的新知识阶层。他们深受西方(以及后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和侵略影响,因此他们寻求通过建设强大的国家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鼓励民众将自己归于“受害的(victimized)”中国国家的组成部分,从而产生民族凝聚力(national cohesion)以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共同的抵抗,并为他们的权力要求提供合法性依据。例如新中国的领土边界是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剥离部分领土之后,被固定的、缩小的边界。因此中国是一个“受害的”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道义上的要求,因为他们抢走了中华民族的领土。这种反西方情绪,连同现实的帝国主义威胁,最终传播和巩固了中国人的“受害者”身份。
“受害的自我(victimized Self)”
虽然新中国的建立宣告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全部废除,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但是中国“受害者”身份依旧持续存在。尽管对“屈辱世纪”的记忆无疑仍然很重要,但是其主要原因是 1949年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关系。在冷战时期,由于先后与美国和苏联进行对抗,中国与国际社会中的两大集团都产生了疏离感,这导致了一种非常不安全的感觉,即中国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而在冷战后,尽管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占据的地位愈加重要,但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仍然是不清晰的。作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西方大国对他们的自由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成就越来越有信心,甚至将其视为国际政治发展的最终形式,即“历史的终结”2。因此,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将中国从意识形态层面定义为“他者”。其次,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和人权状况抱有批判态度。第三,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崛起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恐惧,从而产生了“中国威胁论”。由于“自我”只能从社会互动中产生,而不能进行先验的假设。因此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他者化”的认知,反过来也影响了中国自身对国际社会的“他者化”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受害者身份。
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非良性互动中一直被一种深刻的“受害者”意识所笼罩,这种意识支撑着一种强大的信念,即中华民族应该得到更好的命运。在后冷战时代,虽然国际社会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以主权平等为特征的国家社会,但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二元对立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组成的“核心”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他者”而边缘化。在中国人看来,这种边缘化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行为。同时,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也造成了一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强烈感觉。因此,在一个被“施害的他者(victimizing Others)”(西方大国)包围的世界中,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日本的情况也类似,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拒绝为其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赎罪,是因为日本缺乏对中国的尊重,因此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不仅是过去的现象,也是延续到今天的状态。
为了对抗国际社会中的“他者”,中国试图通过“受害者”身份来重新获取道德力量。由于受害者一词指的是中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中国对“自我”的描述着重于把中国当做国际政治中一个有原则、有道德的行为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恒定的“自我”意识是,中国代表着和平,中国是一个奉行和平外交战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始终处于一个崇高的道德层面。因为中国“受害者”身份的再现需要将中国与“施害的他者”划清界限,这与中国的道德“自我”意识形成了鲜明的负面对比。
“施害的他者(victimizing Others)”
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记忆外,中国的“受害者”意识还来自于中国对自身形象不被重视、不受尊重的不满。因此,“他者”的身份与这种特殊的自我认同紧密相连,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无原则、不道德的实体。如上所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受害者”身份是其与不同国家互动的产物,而不仅仅限于日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及其侵略历史在中国国家认同形成中确实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人民日报》中,从2000年到2005年6月,其中共有730处提到了抗日战争,其数量远多于提及抗美援朝战争的285处,以及提及鸦片战争的181处。而近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与这些根深蒂固的群体负面记忆之间存在内部的一致性,即一个文明的、被“百年屈辱”所贬低的“自我”。
此外,相比于美国、越南等“他者”,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了更直接的影响和更大的流血伤亡。即使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淡化,并且两国之间有产生和解的可能性,但是日本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否认,反而将日本的暴行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并再现了日本作为“施害他者”的形象。而日本的 “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 revisionism)”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行动都在公共媒体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从而造成了普遍的讨论,加剧了中国人对日本及其帝国主义历史的关注,并且进一步固化了中国对于日本不能正视历史的“他者”形象的认知。
在中国媒体中,日本以三种方式被描述为“施害的他者”。第一,强调中国人民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历史。第二,强调日本的 “历史修正主义”和扩大军力、更新武器等行为,唤起了中国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担忧,从而提醒中国需要持续保持警惕。第三,描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的英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英雄主义事迹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对于日本的道德愤怒感,从而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受害者”。因此英雄主义和受害者的身份是相互依存的。最后,把日本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描绘成“带刺的樱花”,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形象,暗示日本的援助具有高度不道德的一面,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结论
本文首先对近期中日关系历史研究进行了批判,并根据社会理论的“自我-他者”视角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解释。这种方法成功地展示了日本的负面历史形象在中国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已经产生并将继续发挥的作用。为了在一个被边缘化的国际社会中增强自己的力量,中国提出了一个替代的“自我”,即一个有道德但受到伤害的国家。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一个“施害的他者”,而日本就是这个“他者”。最后,更加重要的是,日本右翼知识分子将日本无法正视历史问题从而造成的中国的不满情绪,归因于中国政府的操纵,淡化了日本对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更有甚者,他们甚至希望免除日本需要正视其不光彩历史的责任。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展,这种态度只会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日本真的想与它在东北亚最重要的邻国建立更稳定和友好的关系,它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它的罪恶历史,并对中国的“自我”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